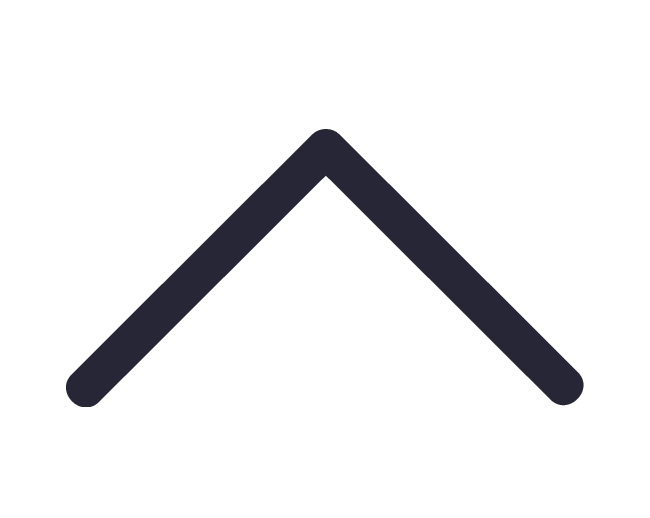(网经社讯)〔摘 要〕微信红包具有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治理学意义。红包产生即时性“领袖”与群众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政治犬儒心理、群体无意识心理和政治感恩心理。红包是产生社会边缘性权力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边缘性权力的粘合剂。红包对社会治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是微信共同体自治的重要动力。红包政治心理影响和决定社会边缘权力、影响社会自治。红包政治社会学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基础性、微观性的影响。
〔关键词〕红包;政治学;权力;治理
作者:张爱军,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安学者,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兼职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5期,原刊责任编辑:周中举。
在2017年之初,微信用户已经近八亿。微信用户剧增,各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微信群必然增加。微信群共同体从性质和类型上划分,具有不同性质和多种类型,如家庭群、亲属群、朋友群、同事群、同学群、师生群、工作群、社区群、官员群、维权群、公益群、价值群、职业群、区域群、生意群、培训群、企业群、同乡群、大V群、微商群、学者群、学术群等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微信共同体从封闭程度上划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闭性强的,一种是封闭性弱的。封闭性强的微信共同体对成员准入要求高,或者知识达到一定水平,或者经济地位达到一定程度,或者同一职业,或者同一价值诉求。进入这种类型的群,必须经由群里人推荐,经群里一定数量人的同意,具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性质,最后还得经过群主同意,否则就不能入群或入群也会被移出。封闭性弱的群则没有封闭性强的那么多规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群员拉进群,只要遵守群规即可。进群的人也是来去自由,自由进群,自由退群。一般而言,进群的人都会发红包,以
无论什么性质和类型的群,几乎都有发红包、抢红包的行为和现象。红包已经成为不同性质和类型群的共同现象。发红包、抢红包都是不定期的,一年四季都会有红包。比较集中发红包的主要是在节日,尤其是春节期间发红包最多。红包已经成为微信群体成员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发红包、抢红包及其相关行为和语言表达等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家庭学等全方位解读。微信政治社会学是网络时代的重要政治现象。微信红包对于微信政治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成为微信共同体的重要粘合剂。微信红包政治社会学是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政治社会参与的一种方式。本文仅从因红包而产生的心理、权力、治理三个维度对红包的政治社会学意义进行分析。
一、红包的政治心理学意义
红包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影响和决定政治心理。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中对政治关系及各种政治现象的主观感受和反应,包括政治情感、态度、心理和行为,体现了人们对政治的信仰与偏好。红包产生了重要的、复杂的、重叠的政治心理现象。它既是对现实政治的反应,也是对传统政治的反应,又是对传统政治心理与现实政治心理的交织性反应。它既是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文化在微信共同体中的延续,又是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折射。这种反应以微观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不但在微信群产生扩散效应,而且还容易转化成现实的心理习惯。
红包产生的心理具有典型的、突出的“即时性”特征,当发红包、抢红包过程结束之后,很快就恢复原有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红包的反复刺激下,不断的即时性就会导致反复性,反复性会导致永久性。巴普洛夫条件反射解说在微信群里就成了红包刺激反射说。因红包引发的永久性行为与心理习惯合为一体,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政治心理而言,发红包、抢红包具有以下的政治心理。
第一,红包产生即时性“领袖”与群众心理。领袖与群众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政治现象,从积极的角度来说,领袖与群众的共生关系,对于维系政治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群众对领袖的服从心理,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领袖离不开群众,群众离不开领袖,二者互相推动。从勒庞的消极角度来说,“领袖”通过断言式、重复式、简洁式的信仰来支配群众。与现实不同的是,在微信共同体群里,“领袖”是通过红包来即时性支配群众的。
在微信群里的“领袖”是不容易产生的,微信的群众也不是群氓式的群众,而是有理性的个人价值聚合体。不同的微信群都是不同的价值共同体,有多少价值就有多少价值共同体。群员往往就共同的话题进行讨论,即使有言论冲突和个人矛盾,在核心价值观上也很少产生激烈的言语冲突和语言暴力。但是,即使价值共同体在核心价值方面不起冲突,也会在核心价值的内容理解方面产生矛盾和冲突。从实际情况来看,发红包、抢红包更容易解决问题,红包不但可以淡化矛盾和冲突,还容易转移和扭转讨论问题的方向。即时性的“领袖”和群众心理就会因此瞬间产生,发红包的人产生了即时性的“领袖”心理和支配欲望,抢红包的瞬间产生了群众心理,各种崇拜式语言、讨好式语言瞬间出现,甚至跪拜的表情包不断涌现。
第二,红包产生即时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核心是施害者与受害者由对立转为共谋。微信价值共同体之间能互相伤害,但不能共谋。微信价值共同体内部偶尔产生的伤害难以产生共谋。从逻辑上说,微信共同体难以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不在微信共同体群之间,也不在微信共同体之内,而在微信共同体之外,而进入共同体之内,某些共同体之内因需要之外的东西而产生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微信共同体之外而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却因微信共同体之内的诉求程度不同,而导致微信群之内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红包会起到调节作用,他们暂时忘记了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角色,他们对发红包者点赞,对抢到红包的大小又吵闹不休。如果通过发红包的方式对微信群进行治理,治理的成本会很低,治理的收益会很高。
第三,红包产生即时性政治犬儒心理。政治犬儒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归顺与臣服,无论是正当的权力还是非正当的权力。发红包即是权力行为,抢红包就是对发红包权力的归顺与臣服。有人在微信群里发红包的目的是为了帮转文章,抢了一分钱红包就必须转,否则就没诚信。转了文章之后则可能是有诚信却没有自信。因而被红包一分钱支配,自信心态变成犬儒心态。这是一个非常怪诞和诡异的行为。在现实中,人们不会因为一分钱而去做事。但在微信中,一分钱,几毛钱,就能支配人的行为。
第四,红包产生即时性群体无意识心理。微信共同体是因为人们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利益诉求、知识诉求、情感诉求、信仰诉求等而走到一起。有些微信价值共同体是自由的理性共同体,有理性的人一般不会陷入群体无意识。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反映在微信共同体中,即发红包、抢红包。发红包、抢红包不应该失去理性,陷入群体无意识当中。可问题在于,红包之微利也会让人陷入群体无意识,尤其是陷入传统政治文化无意识当中不能自拔。这些人虽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在红包之利面前,也会产生即时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理。发红包的人使得抢红包的人瞬时失去了理性,如同被发红包者催眠一样,随着发红包者的心愿走,被发红包者所控制。如果说在现实中,“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那么在微信共同体当中,一切情感、思想、价值都受红包的即时性支配和左右。
第五,红包产生即时性感恩心理。红包里的感恩,不是精神意义上的感恩,而是物质意义上的感恩。感恩本身是一般性和形式性的,感恩的内容却千差万别。红包感恩,如果停留在一般性和形式上,停留在物质层面本身上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背离了人的理性与文明。
即时性有即时性的缺点,也有即时性的优点。即时性的优点在于即时,即时性的心理只要防止转化成永久性即可。这需要群规的约束,需要群员对红包产生政治心理的自觉认识和理性认识。把“领袖”与群众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政治犬儒心理、群体无意识心理和政治感恩心理看成政治心理的即时性“政治眩晕”,通过理性阻断,让微信共同体理性成为常态,非理性成为非常态,就会形成良好的微信共同体政治心理。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什么性质和类型的微信群,解决矛盾和冲突一般会有三个方案,一是群主出面解决矛盾,二是群员非冲突方出来规劝,三是群主或群员提醒相冲突的群员注意讨论规则。在这三个方面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则通过发红包来缓解。发红包与抢红包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表达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发红包具有不同的政治心理,但政治语言、政治图片、政治表情包却有很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比如无论什么样的心理只要抢到红包,往往会有跪拜的表情包或感恩的语言呈现。发红包有相同的心理,政治表情包、政治图片和政治语言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红包心理有的具有政治性,有的没有政治性,只有社会性,也就是说,红包只是微信群员增强联系的一种方式。有政治性的可以归化为政治阶层。政治阶层发红包表现了人们的政治心理,他们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是对政治话语权的把控者。发红包者在红包上写上政治诉求。通过发红包希望引起人们对政治人、政治事件、政治问题的关注。无政治心理的群众可以称为无政治阶层,无政治阶层具有无政治心理。无政治阶层是为发红包、抢红包而发红包、抢红包,他们只关注私人领域的生活,追求自己个体化生活方式,娱乐心理、发财心理、无聊心理,他们对公共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微信群里的语言、图片和红包行为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生活。
二、红包的权利社会学意义
权力社会学的内容之一就是对社会的支配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社会结构、社会分层、阶级分层等都是权力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追求权力、名誉、地位是人的三大本能冲动,因权力能带来名誉和地位,追求权力的冲动成为政治人的首要选项。红包的权力社会学是指红包引发、影响、产生的微信社会边缘性权力。边缘性权力也是权力,人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红包来追求边缘性权力。边缘性权力对于微信共同体的构建、群员的阶级、阶层具有一定的支配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微信共同体社会边缘性权力对政治公共权力具有辅助性作用,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社会边缘性权力既是社会权力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权力的延伸和补充。边缘性权力、社会权力与公共权力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边缘性权力既会影响微信共同体的生态,也会通过外溢影响到社会政治生态。
边缘性权力是指没有在现实中掌握公共权力,却在微信中扮演着公共权力的辅助性角色。这种辅助性角色就应主动为公共权力服务,维护宪法和法律、制度和规则。边缘性权力不是公共权力的组成部分,它在权力的外围边缘,既可以依附于公共权力而存在,又可以脱离公共权力而独立存在。边缘性权力既靠外在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与规则来保障,也需要内在的群规来约束。边缘性权力的主体是群主和发红包人。群主和发红包主体在共同维护宪法、法律、制度和规则时,也是边缘性权力的一部分。这既是微信群政治安全的需要,也是群主和群员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说红包具有经济基础的意义,边缘性权力具有上层建筑的意义,红包经济基础决定边缘性上层建筑,边缘性上层建筑对红包经济基础就具有反作用。红包与权力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红包与边缘性权力的关系。该关系既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正相关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负相关的关系是互相阻碍。红包既可以推动边缘权力地位的提升,也可以使边缘性权力地位下降。边缘性权力既可以使红包发挥良好的作用,也可以使红包失去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包不是微信共同体的终极条件,但它是微信共同体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让微信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但也应该看到,如果有利条件利用得好,边缘性权力作用就发挥得好,否则就走向反面,红包又因此成为边缘性权力的不利条件。
第一,红包决定了边缘性权力的基本属性。虚拟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如果说微信具有虚拟性,那么微信红包却是真实性和虚拟性的统一。红包是真实的,发红包、抢红包是真实的,其名字在微信后台是真实的,在前台却是虚拟的,不是实第四,红包决定了边缘性权力的调和性。不名制的。真实与虚拟使得微信群里人的情感与行为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表现在图片上,也表现在语言上。边缘性权力既是虚拟的,也是客观存在的。红包是真实的,边缘性权力就是真实的。没有红包,边缘性权力只有一种虚拟属性。红包是边缘性权力的重要条件。没有红包,微信共同体也照样存在,但却失去了部分动力。有了红包,微信群体的重要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民间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微信共同体是民间的,决定了边缘性权力是民间的。微信共同体是价值共同体,边缘性权力具有价值属性;利益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红包是民间的,决定了边缘性权力的民间利益属性。红包在群里具有公共属性,也决定了边缘权力的公共属性。公共属性在于维持微信共同体秩序,为群里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准公共权力的特征。社会性与边缘性的统一。红包具有社会性,边缘性权力只是相对现实政治权力是边缘的,对微信共同体本身来说却具有社会性和中心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红包既有政治性,又有社会性。社会性影响政治性,政治性影响社会性。红包是社会行为,却通过社会行为影响了政治行为。
第二,红包决定了边缘性权力的辅助性。政治学的核心是研究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明晰的,即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让公共权力公正执法,在公共的轨道健康运行,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公开的。在微信里,公共权力是隐形的,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身份具有一定程度的隐匿性。显形而具有虚拟性的对公共权力具有辅助性作用的是微信群主。群主的身份是公开的,是群规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群主不断给新人宣传新规,核心是微信群内不能散布违法言论,否则就会被移出群,这就主动地、义务性地为公共权力提供了帮助。群主不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却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公共权力的责任,在权力的边缘和外围为公共权力尽义务。
第三,红包决定了边缘性权力的支配性和服从性。权力的核心是支配与服从。微信边缘性权力的核心也是支配和服从,这种支配和服从没有强制性,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权力既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支配,也可以对人的心灵进化治理等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行支配。对人心灵支配的最好方式就是对财富的支配和控制。发红包既可以支配人的行为,也可以支配人的财富,通过支配财富支配人的话语。
第四,红包决定了边缘性权力的调和性。不同的群即使有价值和利益矛盾,因为微信群中的封闭性,基本上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引发矛盾和冲突的是同一群里的成员。在同一个微信群里,只要只要群主把组群的任务完成之后退出,微信群也会正常运行,群里成员也会进行理性沟通。当微信群成员之间出现非理性话语时,有群员发一个红包,往往就能淡化矛盾和冲突。可见,红包对矛盾和冲突的调节能力兴许比群里规劝更有效。
第五,红包决定了边缘性权力的软化性。一个红包,会从心理上强化权力,软化权利。一分钱都会抽空权利的地基,权力的堤坝也会因此稳固。微信政治学的权利变形记,可能就是一分钱。红包对边缘性权力的腐蚀性和对权利的软化性的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如果权力控制了微信,通过红包对权利加以软化,进而助推边缘性权力,其后果也会很严重。
第六,红包决定了边缘性权力的主体多元性。发红包的人就成了边缘性权力主体。边缘性权力主体多元化,一个方面表现在不同的微信群,另方面表现在同一微信群。不同群边缘权力主体多元化是因为有不同的群主,边缘权力具有多元性。同一群里的边缘权力多元化,主要的原因就是红包。红包的出现,使边缘性权力主体多元化。红包会打破边缘性权力的平衡关系,在客观上让群主变成群员,失去组织群员的能力。谁发红包,谁的权力就大。谁发大红包,谁的核心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就大。群里很多人发红包,边缘权力就会出现多中心化。
任何群员都可以对边缘性权力进行挑战,挑战的表现方式就是使群主边缘性权力更加边缘化,使发红包、抢红包的人不间断地、即时性地主导边缘性权力。值得警惕的是,边缘性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如果不断地受红包的侵蚀,边缘性权力也会滥用。如果边缘性权力没有受到群员的制约,边缘性权力具有成为绝对权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红包既是对边缘性权力的经济约束,又是对边缘性权力的放纵。边缘性权力会利用发红包的行为助推各种心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
三、红包的社会治理学意义
社会治理学是研究社会治理规律与机制的学说。它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等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网络治理包括法治治理、自治治理、新权威治理、社会治理等四个组成部分。微信治理是网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治理方式互相交织,共同发挥立体式、多维式的作用。
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较而言,微信自治式治理是网络治理的主要方式。如果说微信群具有自治特点,丰富了民主政治的形式,那么红包对微信自治具有重要的意义。红包对微信自治具有正向意义,也有反向意义。
(一)红包微信的正向意义
第一,发红包让自治群规成为群员有效约束机制。群规大部分是由群主和群员共同制定的,也有群主单独制定的,这都对每一个群员尤其是对后加入的群员具有平等的约束性作用。当群主或者群员引进新群员时,经常发一个小红包引起群员的注意,在抢红包的同时也认识了新群员,还时常有通过发红包的方式欢迎新群员。每当微信群员违背群规,言论发生激烈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群主或者直接“艾特”所有人,让所有人遵守群规,或者通过发红包的方式提醒群员注意群规,发红包比直接规劝更有效。
第二,发红包激发公共理性。微信群体相对其他群体来说具有封闭性,相对于本身群体来说具有开放性,向所有成员开放。理性是基于事实的判断与推理,公共理性是基于公共事实的判断与推理。群员讨论的话题都具有公共性,都会基于公共事实进行判断和推理,判断推理会引起结论的不同,从而会引发冲突和矛盾。发红包具有激活和让群员关注公共理性的作用。通过发红包让群员对公共性发表公共意见,表达公共立场,培养公共理性。
第三,发红包激发公共德性。每一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独立的人格还需要德性的底线。公共德性在于互惠性。没有公共德性,就失去了讨论公共问题的根基。公共德性的培养,一方面需要群体的互动,理解和掌握讨论的边界,另一方面需要红包的提示与警醒。红包让“利己主义的冰水”逐渐消失,让德性的互惠发挥作用。发红包是利他的,抢红包是利己的,抢红包的利己如果不能转化为利他与互惠,就失去了公共德性。发红包、抢红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基于公共德性,而非个人私利。那些失去公共德性的群员,不会得到尊重,只会失去政治尊严。
第四,发红包实现了微信群生动活泼的局面。毛ZD说:“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对于微信群来说,也要造成这样的局面。微信群最活跃的时刻,是发红包、抢红包的时刻,同时也是参与讨论最活跃的时刻。即使有些群员不参与讨论,也会引发群员对某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还有的群员在发红包时,红包上写有关于某一公共问题的标志。群员在抢红包时自然会加入讨论行列。
(二)红包微信的反向意义
第一,发红包破坏了群员的平等。社会是分层的,微信群员也是分层的,每一个层级的人对平等的感受不同,诉求也不同。社会的分配不公、社会的不平等会通过微信发红包的方式得到部分反映。在微信群里,发红包的人往往容易引起更大的关注,不发红包的人往往不容易引起关注。引起关注的人不但群里社会地位提升了,政治地位也会相应提升。群员人人平等变成了人人不平等。不发红包的人地位明显下降。这种地位既是显性的,也是隐性的。显性的是让人们看到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发红包者大部分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不发红包的人也有各种具体原因。一次性发红包并不会让人感受到不平等,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也会发红包。多次发红包且红包较大就会让人产生经济不平等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甚至会引发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讨论,引发社会不公平感。
第二,发红包助长劫富济贫心态。在微信群里,每一个人人格都是平等的,因为发红包,不但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还会导致群员微妙的心理变化和语言诉求,其表现方式为抢红包的人越来越要求生活条件好的或者爱发红包的人不断地发大红包,最后甚至形成心理依赖和打劫心态。每到过年过节或者有点喜庆的日子,都希望生活条件好的人发红包。经常发红包的人也会因为群员的吹捧与赞美而产生土豪心态和行为。于是,有些群员不停地发,另外一些群员不停地抢,导致发红包和抢红包的人心态都失衡,发红包的人希望不断地得到赞美,抢红包的人希望不断地获得心理安慰,弥补心理落差。
第三,发红包可能助长贿选。通过红包进行贿选是值得警惕的一个重要现象。表面上红包贿选是一个无害的行为,实质上红包贿选是一个有害行为。这是现实贿选现象在红包群里的延伸和复制。红包贿选甚至比现实贿选更严重,影响更恶劣。贿选红包上限仅二百元,抢到每个人手里的钱远远低于二百元,有的甚至只抢到几毛钱或者几分钱。为了几分钱去贿选在现实中是对人的侮辱,在微信群里却成了一个奖励。不发红包就不参加选举,发了红包且能抢到就去选举投票,这或者是选举微信群里的委员,或者是给发红包的人的亲戚朋友投票。这不但会助长贿选行为,而且还可能腐蚀群员的心灵。
第四,抢红包助长了人们的自利行为。自利会破坏自治。发红包本就一个心情,也需要良好的健康心态。可是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金钱至上者看来,有红包就抢,有的甚至还用好几个手机抢红包。从政治上来说,发红包的本意是为了让人们去讨论公共话题,就政治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意见和观点。微信共同体的无政治阶层即使不关心政治,也要遵守公共伦理和公共德性。何况政治到处都是,任何人不关心政治,政治却会关注任何人。但由于群规的软约束,一些群员没有互动和互惠的公共底线,就是为了抢红包而抢红包,从而使得微信共同体的自治失去意义。
第五,发红包会助长语言暴力。语言暴力会破坏微信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关系,也会影响微信共同体成员的多寡。当微信上传播的事实庞杂模糊、信息繁琐难辨时,人们便会借助自己的情感来寻找那些言之凿凿的宣言、价值、伦理、意识形态,使之符合个人的情感与宗教信仰。任何社会议题或问题都会从事实的争论转变为“情感的困斗”。在这种情况下,发红包可以缓解“情感的困斗”,但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情感的困斗”。发红包本是一个善意的行为,善意的行为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而导致语言暴力,甚至还会引发现实中的暴力事件。这或者是因为应该发红包的人没发红包,或者是因为发红包的人发红包太少,或者轮到抢红包的人发红包时消失或者退群。群员中的语言暴力让人失去理性,增加仇恨。公共讨论变成相互攻击和谩骂。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群规、群主和群员的规劝。毕竟微信共同体的生活也是一种社会性的人类美好生活。
总之,微信红包引发的政治社会学意义是多方面的,政治心理学、权力社会学和社会治理学是其基本的组成部分。红包政治心理影响和决定社会边缘权力。红包政治心理影响和决定社会自治。社会边缘性权力和微信自治也会影响红包的发放。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相渗透。红包不是万能的,它只在微信共同体里发挥作用和影响,而且这个作用具有正向和反向的特征。但红包的穿透力和影响力却对现实社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会影响现实的政治社会行为走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红包引发的政治心理对边缘性权力和社会自治的扭曲,需要进行不断地矫正,否则就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