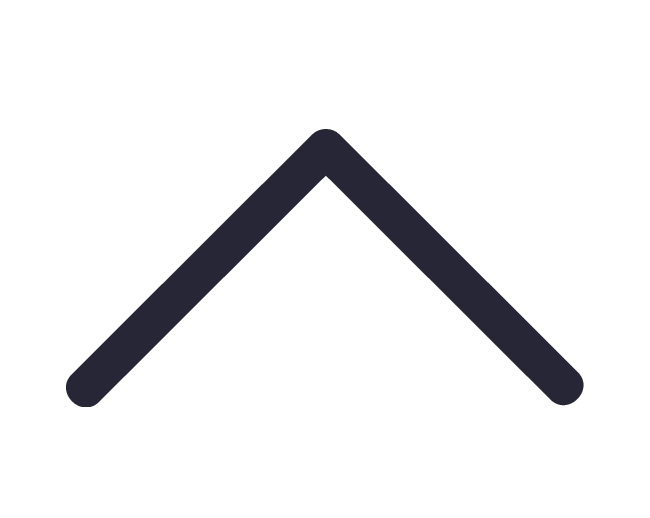(网经社讯)【摘要】不同的数据承载着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也具有不同的价值。大型数字平台在经营时间和客户规模上具有的优势,使其可以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地跟踪市场信息变化,长期地从信息中提取价值。并且,大型数字平台可以利用其已有的垄断力量从获取的信息中攫取更多的利益,这将进一步巩固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解决数据垄断问题,需建立数据共享规则,明确平台数据的权利体系,规范数据收集的同意条款和收集范围,建立数据开发与信息保护相平衡的机制,从而加强对数据垄断的监管。
前言
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人类正在进入数据爆炸年代。数字经济的兴起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有密切的联系,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使人类日益数据化。大量机器生成的数据和个人行为数据被收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手机、汽车、可穿戴设备、家庭路由器、摄像头、传感器等记录下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在线和离线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而随着社交网络服务(SNS)、用户生成内容(UGC)、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等的普遍兴起,个体也在网络上发布越来越多的个性化数据信息。[1]这种情况经常被称为“大数据的兴起”(The Rise of Big Data)或“数据化”(Datafication)。[2]大数据如此重要,甚至有人创造出“数据宗教”(Data Religion)之类的术语。[3]然而,数据并没有实现共享精神。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现,互联网正在违背互联精神,大型社交网站对用户从网络其他部分发布的信息进行屏界。它们通过将用户披露的信息汇总到数据库中,并重新利用这些信息仅在自己的网站内提供增值服务。在蒂姆看来,这些提供商创建的封闭的孤岛可能导致网络的分裂,并威胁到其作为单一的普遍信息空间的存在。[4]
平台收集了大量数据,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优势。对于平台而言,数据是一种可以强化其垄断地位的战略性资产,因为平台在一个领域收集了大量数据之后,在进入另一个新的领域时,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作为战略性投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在新领域占据垄断地位。欧盟委员会指出,数据能够强化平台的间接网络效应,导致企业越来越依赖在线平台,而平台则成为市场和消费者的“看门人”,[5]能够将数据垄断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Sokol, D. D.和Comerford, E. R.[6]指出,虽然关于大数据及其对消费者和竞争的真正意义的辩论越来越激烈,但是,在学术上,尚缺乏在规制政策方面的深入学术研究,在政策实践中,迄今为止,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DOJ)、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或竞争总局(DG COMP)对数据垄断问题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调查意见。[7]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据垄断治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止平台垄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在理论上对数据垄断问题作出梳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解决数据垄断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数据垄断的含义及具体表现出发,梳理分析数据垄断的理论争议、数据垄断的全球治理实践,提出规制数据垄断的政策建议。
数据垄断的含义及具体表现
数据垄断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平台通过数据收集隐蔽化、平台数据产权化和数据利用黑箱化等手段,实现了数据量的垄断和基于数据的垄断。[8]因此,数据垄断至少要分为两个层次。[9]
一是数据量的垄断,在数字经济领域,平台利用其用户优势、技术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等,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虽然数据使用在理论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加密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制度上数据共享机制的缺乏,使平台能够垄断一定的数据量。从成本结构上看,收集和存储数据意味着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这容易产生数据收集和存储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10]这本身会加剧数据量方面的垄断。正如Ezrachi, A.和Stucke, E. M.所指出的,数据的经济学性质,使其有利于市场集中和支配地位。然而,从现实来看,对数据量的垄断分析,需要一个定义完备的数据市场,这个市场目前仍没有广泛形成。二是以数据作为强化垄断的工具。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够实现一次收集、多次使用,在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能够在多种业务线上同时使用,且多次使用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而且,数据使用具备正反馈效应,在使用过程中还能够产生新的数据,这对平台的垄断具有强化作用。在互联网平台应用实践中,数据垄断更多表现为利用数据提高竞争优势、侵害消费者权益、破坏竞争秩序等行为。因此,从本文的研究视角来看,研究的重点将放在“以数据作为强化垄断的工具”这个视角来研究数据垄断问题。[11]数据作为强化垄断的工具,主要是数据能够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并能够成为市场进入的壁垒。
利用数据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并实现精准定价。通过收集、分析和汇总大量数据,公司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并将其活动扩展到新的领域。一位欧盟数据保护监督局的官员表示,“在数据应用方面,政府与商业机构已突破了提高产品质量并将其活动扩展到新‘真相挖掘’的路径。人们的生活经历、社会交往甚至是所思所想都可以转化为算法模型里面的数据源”,由于在较大的数据集上进行训练时,机器学习会产生更好的见解,因此,拥有大量数据访问权限的公司可以以访问数据受限的公司无法做到的方式提高服务质量。[12]
另外,数据要素的使用也不同于其他要素。数据要素通常是作为用户在平台或关联用户上进行交互的副产品而生成的。该数据又用于改善平台提供的服务。因此,在用于处理数据的算法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最多数据的平台将更加高效。这为大型企业提供了类似于“干中学”的优势。[13]例如,网络地图服务通过对用户进行地理定位来获取交通状况信息,然后在将来的查询中再将其推回给用户。类似地,搜索引擎通过其用户在搜索结果页面上的点击(以及更普遍的行为)来“学习”特定网站与特定查询的相关性。反过来,他们的行为会影响相关查询的搜索结果排名,以造福将来的用户。诸如Netflix或Spotify之类的内容提供商广泛使用推荐系统有关先前用户与标题和歌曲的互动信息来提供播放列表,并且以增加未来用户互动的方式对目录进行排序。因此,一方面,平台可利用有关特定消费者过去行为的历史数据,来改善向同一用户提供服务的精准度与质量。如果用户成为某一平台的客户已经一段时间了,则该平台会了解他或她的品味,并且可以使他或她偏爱的商品或服务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平台可以使用来自其他用户的数据来提高向每个用户服务的质量。
在实证研究中,Bajari等[14]使用亚马逊的数据提供了关于数据规模能否带来更准确预测的实证研究,使用具有两个维度的数据为统计模型提供数据:同一类别的产品数量N和特定产品待售的期间T。有关先前预测和零售数量随后实现的其他数据可提高特定产品零售预测的准确性。他们还发现,通过添加相同类别其他产品上的数据进行扩展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此,他们没有找到支持“反馈回路”假说的证据,在该假说中,大型零售商通过出售许多产品而具有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是时间维度(一个特定产品销售了多长时间),学习曲线很快变得平坦。
数据要素通过改善质量从而提升垄断优势的特征,使其在具体垄断表现方面不同于既有的垄断市场。通常,垄断带来的危害是价格上涨,产量减少或质量下降。但数据垄断往往是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Stucke E. M.[15]指出,从表面上看,数据寡头(Data-opolies)几乎不会对这些危害造成任何风险(如果有的话)。与某些药品不同,数据寡头不向消费者收取高昂的价格。谷歌和Facebook的大多数消费产品表面上都是“免费的”。数据寡头的规模也可能意味着更高质量的产品。使用特定搜索引擎的人越多,搜索引擎的算法可以了解用户的偏好越多,搜索结果的相关性就越高,这反过来又可能吸引其他人进入搜索引擎,并且肯定的反馈持续不断。但是,从其他方面看,平台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种质量改进优势,强化其市场地位,从而损害市场竞争秩序。
除了提升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之外,利用大数据还能进行精准定价。例如,通过利用数据不断测试与研究,亚马逊算法模型已经找到了在不同维度的衡量标准下特定人群的消费模式。当前,亚马逊掌握的用户数据数量要远远超过其他零售商的数据储备。海量的用户数据支持着亚马逊进行各种营销实验,而它所能提供商品的价格水平也将在动态调整中更加贴合不同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线上商品价格调整的频率将增加,而产品推荐页面也将改造成更好迎合不同消费者个人喜好的个性化样式。至于价格优化,那更是不言而喻。
当精准定价被平台利用到极致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平台针对每个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个性化定价,这就是新闻媒体常说的“大数据杀熟”,据媒体报道,在我国的网购平台、在线旅游、网约车等平台均不同程度出现过“大数据杀熟”的情况,这些情况正是平台利用其数据垄断地位优势,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表现。[16]
对消费者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强化竞争优势,并使消费者对平台服务形成依赖。数据能够作为创建定制服务和产品以及提高制造效率的输入。[17]很多在线平台提供的交易撮合服务,由于平台上有很多服务提供者或者卖家,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选择,消费者面对如此之多的选择时,容易产生选择困难症。这样,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消费者提供高效的匹配。对于拥有大量用户数据的平台而言,他们可以根据消费者自身的数据进行消费者画像,并根据与消费者相关联的其他人的行为数据等,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精准的个性化推荐和匹配。
数据使用会带来消费者的锁定,而这将进一步优化面向消费者的服务,带来更长时间的应用。数据使用可以挖掘新的用途或者客户需求,增加数据价值,降低数据成本,网络效应将带来数据的横向扩张(增加新的用户以及数据),从而强化平台市场力量。平台拥有对消费者行为进行预测与控制的能力,使原有的关于竞争的理念以及反垄断方法都面临着挑战。例如,2020年7月,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参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上作证说,“竞争只有一键之遥”(only one click away)。他作证说,进入障碍不存在,“使用Google是一种选择(也是免费的),并且消费者浏览www.kayak.com、www.nextag.com、www.bing.com、www.yelp.com、www.expedia.com或任何其他网站并没有障碍”。如果进入门槛确实很低或不存在,那么谷歌不会垄断搜索引擎市场,因此,就不会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然而,谷歌拥有非常丰富的消费者数据,且这些数据来源于多个相关服务领域,这使谷歌在搜索结果排序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这也奠定了谷歌在搜索市场的垄断地位。
数字平台通过利用大数据,将放大消费者的非理性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Simon认为,人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因此,消费者在网络环境下往往不会作出最优决策。[18]在平台数据垄断的背景下,消费者心理偏差的作用被放大,消费者更容易被互联网平台诱导,从而无法作出最优决策。[19]数字平台往往利用其垄断地位以及平台作为看门人的地位,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诱导,从而强化其垄断地位。Jamie, L.和Jacob, L. S.[20]发现,互联网平台普遍存在着“暗模式”(Dark Patterns),即互联网平台在用户界面故意混淆用户选择,使用户难以表达其实际偏好,或操纵用户采取某些行动。研究指出,精心设计的隐私条款和界面,能够使相关条款的接受率提高228%,针对一些特定人群的则可以使接受率提高371%。由于暗模式如此有效,研究者指出,即使谷歌如此强大,为了成为iPhone上的默认搜索引擎,也得每年向Apple公司支付120亿美元。默认设置问题在数据垄断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而几乎没有人研究。[21]例如,有证据表明,社交媒体等令人上瘾的技术具有产生危害的特征,这对反托拉斯执法构成了挑战。[22]从平台发展现实来看,很多购物平台以各种促销等方式,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欲望,甚至使之购物成瘾。信息类平台等持续向用户推送其感兴趣的内容,从而产生“信息茧房”效应。还有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从而使用户对平台的内容与服务形成依赖,并产生成瘾效应。国外的调查报告也表明,网络平台正在利用个人的认知偏见,促使在线消费者购买他们不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或者透露他们不愿透露的个人信息。[23]这也说明,平台数据垄断问题,对用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需要更进一步的治理。
数据作为潜在的进入壁垒。由于数字经济的特殊性,数据和分析能力可能成为进入数字市场的重大障碍。为了保持数据相关的竞争优势,相关公司花费大量资金和精力来获取和分析数据,这本身可能成为进入壁垒。市场结构会发生变化,少数大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并有机会大幅增长。而且,这些障碍可能会自我强化,从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评估数字市场中的合并要求执行者考虑除短期价格影响之外的许多因素。一个关键因素是数据的竞争重要性及其作为进入壁垒的潜在作用。[24]
如前所述,平台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反馈越多,就越能改进其产品和服务,则他们越能将其技术与客户的偏好相匹配,相应地竞争优势就越大。因此,为了有效竞争,平台可能需要最低水平的客户反馈,以便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客户的需求。这个最低水平的客户反馈,就构成了对平台进入新市场的壁垒。
从互联网发展的现实看,很多平台在前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数据,通过利用这些数据,平台可以持续优化其服务,这对新进入市场的竞争平台构成了进入壁垒,在这种背景下,新平台面临着更高的进入成本。
数据垄断的理论争议
虽然数据垄断问题在数字平台中广泛存在,并形成了普遍的现实影响,然而,在理论上,对数据垄断仍有较大的争议。
一种批评的观点是,数据本身并不稀缺,单纯依赖数据,很难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25]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积累速度加快,数据量极大丰富,因此,数据并不会被少数平台垄断,这样,数据垄断理论本身值得怀疑。[26]Tucker,S. D.和Wellford,H.[27]指出,重要的数据集“已经变得如此便宜,甚至对于原型基于车库的初创公司来说,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因为“相关数据可以广泛获得并且通常是免费的”。
另一种批评的观点则认为,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本身具有由所有者垄断使用的特征。曲创[28]指出,除了公共领域的数据之外,企业拥有的数据可以明确属于公司,因此,天然属于其拥有者使用,不存在垄断与否的命题。有意思的是,另一派学者则从数据不具有排他性的视角来否认数据垄断问题。例如,许可指出,数据没有法律上的所有者,并不能排他使用。[29]因此,数据垄断问题并不能成立。两种理论虽然假设上完全相反,但是,其得出的结论却具有相似性。
我们认为,数据垄断不仅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案例。从理论上看,由于数据要素的特殊性,拥有数据要素的企业可以通过数据运用获得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垄断地位。数据的一大价值便在于它所承载的信息。信息在市场中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在现代信息社会其地位更加凸显。科技巨头所获取的数据量相比小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意味着科技巨头对于市场需求信息拥有小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不同的数据承载着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也具有不同的价值。大型数字平台在经营时间和客户规模上具有的优势,意味着可以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地跟踪市场信息变化,长期从信息中提取价值。并且,科技巨头在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上也具有优势,更容易从搜集到的数据中挖掘出更多的信息。由于数据和数字产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大型数字平台可以利用其已有的垄断力量从获取的信息中攫取更多的利益,这将进一步巩固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
李尔试验室在2019年为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提供的咨询报告中提出,[30]数据的使用可能产生基于规模经济的“正反馈回路”(positive feedback loop):其一,拥有较大安装基础的公司能够积累更多的数据;其二,更多数据可以改善服务;其三,改进的服务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获得更多的数据等。这个正反馈回路说明数据在强化平台垄断地位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否把这些作用发挥出来,取决于数据可替代性(Data Substitutability)、数据互补性(Data Complementarity)和数据的规模报酬(Data Returns to Scale),数据的可替代性越强,则数据在作为垄断优势方面的作用越弱,数据的互补性越强,那么组合各种数据可能会带来优势。数据的规模报酬越大,所在企业的优势越明显。Graef,I.[31]进一步指出,数据与垄断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分析数据,在位者可能能够检测消费者偏好的趋势和变化,从而能够开发可能产生新市场的新产品和服务;二是数据可能是现有在线平台提供商竞争对手引入的产品和服务的必要输入;三是由于个人数据正在取代价格作为互联网上的货币,与价格相关的伤害理论可能转换为数据。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数据垄断在实践中的应用。例如,Zhu和Liu[32]发表了关于亚马逊产品类别进入策略的实证研究。作者使用22个子类别中在Amazon.com上出售的163853种产品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亚马逊确实可以轻松检测到热门产品类别,进而进入到该市场。
综上,我们认为,数据正成为平台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正如谷歌首席科学家Peter Norvig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算法,我们只是拥有更多的数据”。[33]数据垄断正在成为平台规制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需要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数据垄断规制的全球实践
正因为对数据垄断所带来后果的担忧,世界各国已开始对平台数据垄断问题进行规制。2021年6月,欧盟启动调查程序,调查谷歌是否通过技术手段打压在线广告领域竞争对手,调查重点是谷歌是否限制第三方公司获取用户数据,同时将数据留给自己使用,从而扭曲市场竞争。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联合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对Facebook数据垄断问题进行调查,其理由是Facebook可以使用从广告商活动中收集到的用户偏好信息来调整自己的分类广告服务Facebook Marketplace,Facebook以扭曲竞争的方式使用数据,特别是使用从广告商那里收集的广告数据,以便在分类广告等Facebook活跃的市场上与它们竞争,从而给Facebook带来了不应有的竞争优势。2021年5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FCO)根据新的反限制竞争法(GWB),对谷歌展开调查。其理由是,谷歌的一系列基本数字服务,如搜索、YouTube、地图、Android和Chrome,“可以被认为对跨市场竞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谷歌的数据收集做法是否为其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是否具有反竞争性。202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通知亚马逊,认定亚马逊“系统地”依赖从通过其市场销售的独立公司收集的数据,然后利用这些数据使自己与这些公司竞争的零售业务受益,这违反了欧盟竞争规则。2020年,意大利竞争管理局(AGCM)对谷歌的展示广告业务展开了调查。认为谷歌“歧视性地使用通过各种应用程序收集到的大量数据,从而阻止竞争对手有效竞争,并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2016年3月,德国联邦卡特尔办公室(FOC)针对Facebook涉嫌通过违反德国数据保护规则而触犯了该国的竞争法(涉嫌滥用支配地位)。2019年7月,德国反垄断机构认定Facebook在多项业务中交叉利用数据,违反了反限制竞争法和数据保护法。2020年6月23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Facebook滥用其在社交网络市场的主导地位违反了德国竞争法。该裁决维持了FOC的决定。
还有一些监管关注了并购过程中所形成的数据垄断问题。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11月发起的谷歌调查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涉及以可能违反欧盟竞争法的方式获取个人数据:其一,通过排他性协议获取个人数据。其二,以防止数据可移植性。在Apple/Shazam合并案中,欧洲委员会使用四个相关指标将当事方收集的数据与市场上其他可比较的数据集进行了基准比较:一是组成数据集的数据的多样性(多样性,Variety);二是数据收集的速度(速度,Velocity);三是数据集的大小(数据量,Volume);四是经济相关性(价值,Value),[34]将数据垄断问题正式纳入到并购审查中。
在立法实践中,2021年1月通过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GWB)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对评估市场支配力程序的拟议修改。在确定支配地位的过程中,主管部门现在必须考虑实体的“财务实力及其对竞争相关数据的访问”以及其他更传统的标准,如市场份额,[35]这说明在立法对数据垄断问题进行了正式规定。2020年底,欧盟发布了“数字市场法”草案(The Draft Digital Markets Act, DMA),该草案对处于看门人(Gatekeepers)地位的数字平台在数据使用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参见DMA的第5~13条),包括:看门人平台应避免将源自核心平台服务的个人数据与来自看门人平台提供的任何其他服务的个人数据或与来自第三方服务的个人数据相结合;看门人平台与业务用户竞争时,不能使用业务用户通过活动生成的任何非公开可用的数据。这是对看门人平台提出的一个严格要求。
在美国,数据垄断问题也受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2021年2月4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Amy Klobuchar提出了2021年竞争和反垄断执法改革法案(CALERA)。[36]该法案回应了很多当前平台垄断与竞争中的热点问题,包括平台利用数据强化其垄断地位的问题。2021年6月,国会议员Mary Gay Scanlon提出ACCESS法案(Augmenting Compatibility and Competition by Enabling Service Switching),[37]该法案要求平台允许第三方将数据传输给他们的用户,或者在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传输给竞争企业。同时,还要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建立技术委员会,以颁布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标准。美国家具制造商威廉姆斯—索诺玛(Williams-Sonoma)于2018年12月对亚马逊提起诉讼,指控亚马逊会根据其在平台上收集的数据来预测消费者想要的产品,并以其品牌名称介绍这些产品,最后偏向其搜索算法,以偏向于自己的产品而不是独立的商家。
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数据垄断问题。2021年2月7日,中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38]是全球第一个系统性对平台垄断问题进行规定的法规,对数据垄断问题有着直接的规定。该指南第十七条规定,平台“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差别待遇,将受到反垄断规制。在2021年8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个人数据收集与处理、“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有着明确规定,从而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数据垄断规制体系。例如,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加强对数据垄断监管的政策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数据垄断会给平台进入到新市场带来初始质量差异,而这一初始质量差异,可能会带来市场的集中。深入考虑数据垄断的影响,需要更进一步对数据垄断问题进行规制与监管。Prufer J.和Schottmuller C.[39]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基于数据垄断而形成的市场主导地位是持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市场出现倾斜,实力较弱的公司在未来将永远不会获得超过可忽略的市场份额。如果需要持续不断的,少量的创新投资来保持消费者的感知质量恒定,那么该市场甚至会出现爆发式增长。然而,正因为平台能够建立这种基于数据的竞争优势,他们对更深更前沿的技术研发缺乏投入。从这个意义上看,支持数据垄断的理论基础,即数据垄断可以促进数字创新,已不能成立。James Cooper指出,反垄断法是监管大数据的不当工具。因此,有必要对数据垄断进行规制。[40]
建立数据共享规则。从监管的视角来看,打破数据垄断最有力的方式是数据共享。数据共享具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消费者侧的数据共享,即数据的可携带性(Data Portability,有的文献将其翻译为“数据可移植性”)。消费者可以将其在一个平台上生成的数据,携带至另一个平台,这样相当于消费者的数据在平台之间实现了共享。或者消费者可以允许各个平台对其数据进行互操作。[41]从2018年5月开始,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将规定公司有义务使个人在使用在线服务退出时,能够随身携带其个人数据。这相当于将数据垄断监管问题转向事前竞争执法中的预防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消费者越容易将其数据从一个提供商转移到另一个提供商,或者授予新提供商对其数据的访问权,竞争对手就越容易攻击基于数据的市场力量。因此,必须引入主导平台的明确行为规则,加强数字部门合作的法律确定性,加强竞争法与其他数字法规之间的制度联系。另一种是基于生产者的数据共享。也就是说,平台将其所拥有的消费者数据共享出来。为了给平台收集、存储数据提供激励,理想的数据共享方式是建立数据市场。也就是为个人数据创建一个新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人们将拥有他们提供的信息并将其出售给想要使用它的平台。但是,数据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得建立数据共享市场的成本非常高,因为数据的原始控制者在数据售出之后,很难控制其被再次出售。因而,与生产者数据共享相关的一种可行模式是强制共享。如果拒绝访问数据成为一个反竞争问题,竞争法可能无法确保有效执行。因此,根据现行法律,拒绝访问数据可被视为滥用市场支配力,原则上可以强制进行数据访问。具体而言,应通过制定进一步的开放数据法规来要求所有公共机构通过标准化平台和开放的可互操作数据格式提供结构化数据,来改善对公共数据的访问。此外,应制定有关公共部门数据的收集,使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总体数据战略,受托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司应承担提供获取信息的义务。同时,应强制市场主导型在线平台,以可互操作的格式实现用户的实时数据可移植性及其用户的使用数据,并确保与其他竞争者提供的补充服务的互操作性。因此,破除数据垄断,首要的是建立数据公平使用机制,实施数据共享,打破数据壁垒。数据共享的核心是要建立公益性的、共享的数据交换机制。在数据壁垒还没有形成之前,必须抓紧时间建立。如果数字平台的相关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再建立就很困难,改革的阻碍将更大。故而,我国应抓紧当前的时间窗口,加快建立数据保护与数据共享机制。
明确平台数据的权利体系。在数据垄断规制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明确用户在平台上的行动轨迹所形成的数据所有权问题。联合国等机构认为,用户应该对其在平台上所形成的数据拥有权益(并不一定是所有权);欧盟认为,用户对其在平台上所形成的数据有着控制权,例如,可以要求平台遗忘其所形成的数据或信息(被遗忘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倾向于用户对数据拥有控制权。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即使明确用户对数据的控制权,如果产权规定不明确,很容易导致平台将数据作为其私产。而且,即使在现有的控制权方案,也没有包括数据的迁移权,用户因为没有对其数据的所有权,也无法向平台提出自己的要求。因此,既要避免平台将数据产权化,作为平台的私有财产;同时为了鼓励产业发展,也应承认数据收集者、控制者对数据的利用、开发等享有适度的权利。
规范数据收集的同意条款和收集范围。数据垄断往往与平台过度收集数据有关,因此,应就数据收集的同意条款、收集范围等建立明确的规范。核心的问题是要把数据收集条款明示化,防止过度收集数据。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对信息收集的明示同意比较重视,已有完备的体系,但需要对相关收集条款等进行更具体的约束。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第十五条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个人有权撤回其同意”。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平台设计了非常复杂的隐私条款,并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过度收集数据。[42]因此,在监管方面,需要出台更细化的管理规定,明确数据收集的明示原则,要求平台明确数据收集的范围等。要对平台将信息收集与提供服务进行捆绑的商业模式进行更精准的监管。由于中国的平台大多采取基本服务免费、增值服务收费的商业模式,这使平台必须大量收集消费者或用户的信息与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挖掘与开发,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增加用户的粘性,并阻止其他平台进入到相同的市场。对平台将数据收集与捆绑的业务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该法第十六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在具体监管中,需要对此法律条文进行细化,将无关数据收集与服务提供进行脱钩,进行更精细化的监管。
建立数据开发与信息保护相平衡的机制。数据垄断涉及到数据开发与信息保护机制的平衡。建立这个平衡机制应该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法律应当始终追求商业价值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平衡。既不能陷入到绝对数据保护的无底洞中,也不能放任对数据的无限制开发与挖掘。二是要对数据保护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合理的评估。尤其要避免把极端事件作为常态,并以此作为监管框架的基础。三是要采取弹性原则,尊重个体的选择。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隐私的态度也产生了很多变化,可能很多人愿意与他人分享原来被视为隐私的东西。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如何避免平台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制收集信息,侵犯用户权益,并确保数字经济市场的竞争秩序。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数字经济基础理论问题及发展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20CJYB01)
注释
[1]Acquisti, A.; Taylor, C. and Wagman, L., "The Economics of Priva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6, 54(2).
[2]Ezrachi, A. and Stucke, E. M., Virtual Competi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Driven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Elkin-Koren, N., "An Intimate Look at the Rise of Data Totalitarianism", Jotwell, Apr. 21, 2015.
[4]Lee, B. T., "Long Live the Web: A Call for Continued Open Standards and Neutrality", Scientific American, 2010, 303(6).
[5]EC,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iiticai/fiies/soteu2018-preventing-terrorist-content-oniine-regulation-640 en.pdf.
[6]Sokol, D. D. and Comerford, E. R., "Antitrust and Regulating Big Data",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2016, 119(23).
[7]自从2019年开始,欧盟和美国均开始对亚马逊利用其在平台上收集的第三方卖家数据优化其自营业务的行为进行调查。德国反卡特尔局也开始对Facebook旗下不同产品的数据进行交叉应用的行为进行调查。
[8]李勇坚、夏杰长、刘悦欣:《数字经济平台垄断问题:表现与对策》,《企业经济》,2020年第7期。
[9]梅夏英、王剑将数据垄断概念区分为数据垄断与基于数据的垄断,其区分方法与本文有着细微区别。梅夏英、王剑:《“数据垄断”命题真伪争议的理论回应》,《法学论坛》,2021年第5期。
[10][33]Carballa, B., "Data as a Comm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a General Policy Poposal", Cepn Working Papers, 2016.
[11]曲创(2019)亦提出,“数据垄断”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基于数据的垄断”,并不是对数据本身的垄断。
[12]Parker, G.; Petropoulos, G. and Van Alstyne, W. M., "Platform mergers and antitrust",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21(1).
[13]Biglaiser, G.; Calvano, E. and Cremer, J., "Incumbency advantage and its value",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9, 28(1).
[14]Bajari, P.; Chernozhukov, V.; Hortasu, A. and Suzuki, J., "The Impact of Big Data on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9.
[15]Steinbaum, M. and Stucke, E. M., "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Standard: A New Standard for Antitrust", Report for the Roosevelt Institute, 2018.
[16]当然,从经济学上来说,精准的个性化定价可能有利于扩大市场交易量,从而增加社会总福利效用。但是,在平台利用数据垄断进行价格歧视的背景下,平台的这种行为将扩大社会交易量,从而减少无谓损失,增加社会总福利。然而,在平台数据垄断的背景下,社会总福利的增加部分或全部由平台获得,这将加剧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并损害消费者福利,因此,纵容平台进行数据垄断并不是一种最优的政策选择。梅夏英、王剑:《“数据垄断”命题真伪争议的理论回应》,《法学论坛》,2021年第5期。
[17]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A New Competitio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Law 4.0", 2019.
[18]Watts, J. D. and Dodds, S. P., "Influentials, Networks and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7(34).
[19]Stucke, E. M., "Behavioral Antitrust and Monopolization",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012. 8(2).
[20]Jamie, L. and Strahilevitz, J. L., "Shining a light on dark patterns",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2021(1).
[21]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 2019,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22]Rosenquist, J. N.; Scott Morton, M. F. and Weinstein, S., "Addictive Techn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ntitrust Enforcement",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Feb. 22, 2021.
[23]U.S. HOUSE,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2020, 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
[24]McSweeny, T. and O'Dea, B., "Data, Innovation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 Looking Beyond Short-Term Price Effects in Merger Analysis",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hronicle, Feb. Volume 2, Winter, 2018.
[25]Lambrecht, A. and Tucker, C.,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ensile Promotions in Digit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6.
[26]许可:《数据垄断真的存在吗?》,《中国信用》,2018年第1期。
[27]Tucker, S. D. and Wellford, H., "Big Mistakes Regarding Big Data, Antitrust Sourc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Dec. 2014.
[28]曲创:《数据垄断的伪命题和真问题》,《科技日报》,2019年8月21日,第8版。
[29]对于数据的排他性,经济学家是存在争议的。从数据本身的自然性质来说,其并不存在排他性。但通过建立某些制度(现实的或想象的制度),并使用加密等相关技术,可以使数据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数据的可排他性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数据自身的技术特征(如加密技术)与法律制度安排。
[30]Lab, L., "Ex-post Assessment of Merger Control Decisions in Digital Markets", Final Report, 2019.
[31]Graef, I., "EU Competition Law, Data Protection and Online Platforms Data as Essential Facility", Summary of PhD Thesis, PhD Degree Obtained on 29 Jun. 2016 at KU Leuven, Belgium.
[32]Zhu Feng and Liu Qihong, "Competing with Complementors: An Empirical Look at Amazon.co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October 2018.
[34]此四个方面即大数据的四个“V”特征。
[35]"Amending German competition law for digital regulation", https://digitalregulation.org/amending-german-competition-law-for-digital-regulation/.
[36]法案原文参见:https://www.klobuchar.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e/1/e171ac94-edaf-42bc-95ba-85c985a89200/375AF2AEA4F2AF97FB96DBC6A2A839F9.sil21191.pdf。
[37]法规原文: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3849/text?r=2&s=2。
[38]《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7/content_5585758.htm。
[39]Prufer, J. and Schottmmller, C., "Competing with Big Data", https://pure.uvt.nl/ws/portalfiles/portal/15514079/2017_006.pdf.
[40]由于数据垄断的特殊性,对数据垄断是否需要进行规制,经济学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Ohlhausen & Okuliar(2015)认为,使用反垄断视角来解决数据问题,可能会威胁到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Ohlhausen, M. K. and Okuliar, A. P., "Competi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the Right [Approach] To Privacy",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15(1)。
[41]互操作性与可携带性不同。Jacques Cre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Heike Schweitzer(2019)定义了互操作性的三种“类型”:协议互操作性,数据互操作性和完整协议互操作性。OMontjoye, Y.,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 2019。
[42]例如,有媒体报道,腾讯微信应用持续读取用户的相册,美团持续读取用户定位信息。